看了进文同志的《哭灵》一文,我的悲痛之情再一次被勾起。六年间,亡母丧父,我经历了人生至暗的两个时段。不解的是,母亡、父丧期间,要不是哭灵人撕心裂肺般的哭泣声撞击我的心扉,让我泪湿双眼,我竟然没有自发地流过一滴伤心的泪水。
是泪点过高吗?显然不是。别人悲戚的哭泣声会引得自己落泪;电影电视剧里悲壮的场景常常令自己泣不成声;抒情歌曲唱到动情处泪眼模糊也是常有的事……都说男儿有泪不轻流,我却偏是个容易落泪的人。
是忘了父母的哺育之情、教养之恩了吗?更不是。天地之间,父母恩情比天高、似海深,羊尚且有跪乳之恩,我一读书人,又怎敢忘了父母的养育恩情?
我的眼泪哪里去了?
母亲和父亲的死,刻骨铭心,怕是到自己死的那一天都难以忘记。
母亲是一位能干的女性。很爱讲究,再累再忙,也要梳洗得干干净净,穿戴得整整齐齐。我们兄弟姐妹四个,母亲把我们个个照料得规规矩矩、妥妥贴贴。家里经常修拾洒扫,屋里屋外无不给人一种舒适的感觉。“地上捡得盐起呢!”邻里乡亲用最质朴的言语表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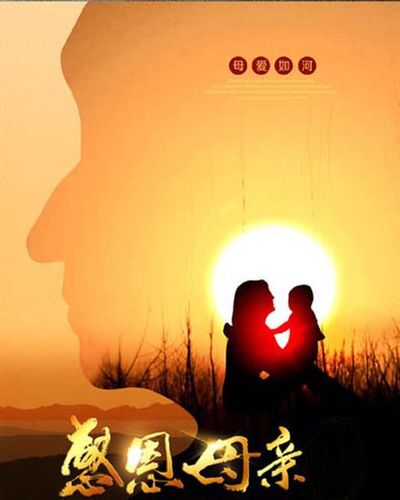
达他们对母亲的夸赞。出集体工挣工分,母亲是队里妇女同志最多的一位。
母亲的友善在亲友和乡邻中更是有名。待人总是一张笑脸。桌上好吃的菜,总是热情地夹给客人。园子里果子熟了,院子里家家送一些,让大家品尝品尝。
母亲身体一向很好。我的印象里,她好像没有生过病。偶尔听说她头有点儿晕,她不会去看医生,到床上躺一下就没事。谁想到,后来居然患了老年痴呆症。痴呆也就痴呆吧,要命的是,有一天,母亲不小心摔了一跤,髋骨骨折了。可怜的母亲啊,被剧痛折磨着,又痴呆得不能配合治疗,生生地痛得只剩下一把骨头,才撒手离去。
父亲辞世时虽然年过九十,已属高寿,然一身病痛,也饱尝了人生的艰辛。
不会忘记,十四五岁上高中时,星期天和假日里随大人们去城步挑脚担。返回的路上,逾接近坐船的时候,逾迈不开脚步,肩膀压得生痛,是父亲放下自己的担子,接了我一程又一程;
不会忘记,父亲在外面做民工,每逢食堂里打牙祭,自己只吃点辣椒、姜片,留着猪肉、鸭肉带回来,给我们兄弟姐妹吃;

不会忘记,父亲当民工在他乡修水渠,病痛发作,被同修水渠的队里人用竹杠抬回家的情景;
不会忘记,父亲青壮年时,风湿性关节痛,家里常住着威溪熊家岭上的草药郎中熊三爷——我们几姊妹称他为“三爷爷”;
不会忘记,父亲一次腰椎间盘突出疼痛,几天卧床不起,我叫了朋友的车送往医院治疗;
不会忘记,父亲辞世前的九天里,在医院治疗,心肺功能严重衰竭,呼吸困难,身子动弹不得,只得强忍不适,日日夜夜保持半坐半躺姿态;
不会忘记,父亲临死前神智不清、痛苦难耐的模样……
想起这些,我的心里就一阵一阵刀割般痛苦!
可是,父母辞世,容易动情落泪的我,竟然没有自发地流下过一滴伤心的泪水。
我禁不住一次又一次问自己:眼泪哪里去了?
(王忠义)
免责声明: 本文内容来源于王忠义 ,不代表本平台的观点和立场。
版权声明:本文内容由注册用户自发贡献,版权归原作者所有,武冈人网仅提供信息存储服务,不拥有其著作权,亦不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如果您发现本站中有涉嫌抄袭的内容,请通过邮箱(admin@4305.cn)进行举报,一经查实,本站将立刻删除涉嫌侵权内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