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人鬼情未了散记


距县城遥远的乡村,寂静而单调。春末夏初,生产队里收麦子、整秧田、犁田耙田,力气用得尽,事情做不完!夜色一降临,累乏了的人们,全都是早早就睡了的。

那时下放乡村,光棍一条。队上的民兵排长,与我年纪相当,我戏称“陶排”,他家喊我吃饭,吃后在他家与他同睡一床。他当了这个小官,大队配给他一盏气灯,有了它,借助昏黄的灯光,入睡前或聊天,或看书——我看着一本什么老书,看得非常入神,同床问我什么事情,也懒得答他。看了许久,熄了灯,漆黑一片,我还沉浸在书中的情节里。

双眼是睁开的,还在思索书里人物的结局,忽的,就见房门开了,扑进一阵冷风,顿感寒意袭身,眼里看见的是一团影子,那飘散的头发是看清楚了的,朝我扑了来,我使劲用双手反击,双腿用劲猛蹬,口里大声斥骂,而且心里非常明白,只有用力蹬醒陶排,才能救我出苦海。一会被我蹬痛了的他,口里连连喊着痛,坐起身子,问道:怎么啦!
我照实说了。他下床去看,门,没有开呀;栓,插紧了的呀!

于是提灯上路,去5里外的村子请医生。出了村口,是一连片的坟山,要是平时,我眼都不会眨一下,自小在敞开的棺材进出自如的我,见坟墓如见草芥,经这折腾,我却有点心虚,总是走在陶排的前面,觉得踏实一些。他也颇解我意,为了壮我的胆,总是挨得很近,放开喉咙与我东扯西拉。他的声音大一些,我心里就好过些。哦,我这间小房子是吊死人的。他平静的补充。

因为什么,什么时候?
很多年了,我还未出生呢。因为两口子淘气。
啊,我心里咯噔一下,觉得一阵寒意袭身。一会,他妈在外面喊:你们快一起去喊赤脚医生——你爸肚子痛得厉害,痛了好一阵了!
——咦,这么凑巧,鬼寻了我,难道又寻了他爹?我在心里嘀咕。

起大风了,吹得嘘嘘叫,混杂着小虫子的细碎叫声,间或传来远处隐隐约约的犬吠声,还没有走出坟山,两边都是密密麻麻的坟墓,暗淡的气灯光影在风中摇曳,忽的映射出一垒新坟竹棍上飘动的钱纸,立马就觉阴气袭人,陶排提灯索性站在坟前,大声喊着她的名字:莲妹子,你不要做鬼哟!




这是邻村一位因抗婚仰药自杀的年轻女子,死了没有10天,读过高中有才气,一大队书记儿子看中她,执意娶她,谁知她已有心上人。父母坚决反对……无可奈何寻死,人死了,留下几句诗尽人皆知。经过她的坟前,想起她的绝命诗,心里的难受莫名其妙的消去了许多!

那一夜好不容易熬过了!几天的萎靡不振,引起陶排父母亲的关切,为我找了师公在那小房子里做法退邪,我要躺在床上闭了双眼陪着,只听得屋子里噼噼啪啪,这响那响,响过一阵,师公便说退了,走了,再不敢来缠你了。当然,我心里就有点悲喜交加,不怕了,我不怕了!击鼓人送鬼,漫天雾送寒。

自此总在回想那个令我毛骨悚然的场景,搜寻那个令人丢魂失魄的模糊物,说不出个所以然,莫名其妙的引发了读鬼诗的兴致,先后读过许多,像:青燐走平沙,独夜鬼相语。松柏愁香涩,南原几夜风;荒郊白骨卧枯莎,有鬼衔冤苦奈何;有时余血下点污,所遭之家家必破;四更山鬼吹灯啸,惊倒世间儿女……至今我还能朗朗上口的背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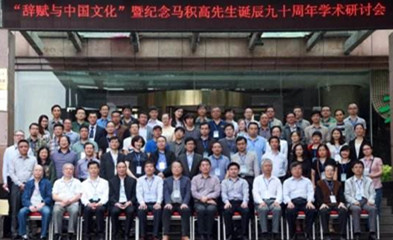
【马积高教授相片】
我下放的那片地方,当时下来了好些落难的名家,大学教授之类,有好几个,湖南师大的马积高教授,就是其中之一,经与他要好的一位知青引荐,结识了他,随着不断的接触了解,成了我的“先生”。初次见面,个子高大的老夫子儒雅客气:年轻人,请多关照,请多关照——带着衡阳腔调的塑料普通话。想学什么,只要你尊重他,准会得到满足,而且轻言细语诲人不倦,他写的《近世500年歌》,就是他写出来教会我的……

鬼神之事,我曾问过马老,他笑眯眯的说:只要你不怕,你就不会怕!老夫子不多说话,怪不得,他在文革中受尽磨难,又遭今日流放之苦,若不小心再说错话,这人生又该如何打发……但是,读书人的斯文,还是让他坚守了传道受业的底线,他让我背熟了明代刘溥的《钟馗杀鬼图》。
半个多月后的一次迷路,又让我彻底经受住邪恶的惊扰与洗礼,重振豪气如虹的心胆!


挑了一担箩筐,步行40余里回家去。翌日返乡,一个人倒也悠然。因为看了一场电影,一路沉浸在电影的回味里,黑了许久才走拢村前一片小树林,距村子两里来路,葬有几座坟,平常出工,也长在此休息的。眼前漆黑,挑担前行,左走右转,右转左走,走走转转,总是转不出林子,找不到进村路——我心里明白了,遇上倒路鬼了。急途自有急计,村人曾教我两个法宝:撒尿,朝四向一顿猛射(那时年轻,力量大得很,要撒多远就有多远):再是大声骂娘。都照做了,又挑担上路,转东转西,还是转不出去!妈的,老子彻底灰心,但绝不丧气,将一担箩筐重重的丢在一边,树上的鸟们受不住,噗的乱飞一气。走了几十里,累了困了,扁担做枕头,倒头就睡……

醒醒,伢崽醒醒,日头晒屁股了——一个熟悉的乡亲声音吼醒了我。揉揉惺忪的双眼,双手两伸,哇的一声打了个呵欠,终于清醒。“哎呀,我的伢崽,你不怕鬼,好大的胆子!”黎明即起,在外干私活的乡亲发现了我!

村里一传开,引发嘘声一片,好事来了:几个五保户先后死去,村人胆大的或嫌肮脏推辞,或胆小不敢近前,让我承包。队长胸部两拍,你搞好了一个,挂5个劳动日,一个0.65元,5个3.25元。犹豫了一刻,英雄战胜了5秒钟的动摇,咬咬牙,决定下海了!洗呀,抹呀,换衣裤呀,有条不紊,在尸体上忙开了……有时外队人死的多,队长还在外头为我挽生意!

也在当年的一个冬天,去邻队陈姓知青处玩。还未坐定,对面坟山上大狗小狗猛烈狂叫,叫叫停停,甚是令人烦躁,而且叫通夜,难有停歇,已经持续10来天。一打听细节,原来是他母亲去世后才有的事。那些狗呢,专门对着他母亲的坟地狂吠。
烧了地契没有?我问。烧什么地契?他不懂,疑惑不已。

找来纸笔,我写了安葬应做的仪式程序,打了一些钱纸,香烛,炮火,备了一点肉做祭品。他陪我去到坟山,我照本画葫芦,口中念念有词。做毕,回到住处。约摸半个钟头后,狗吠声渐渐平息,此后,再无甚风浪。

记得马老问过我:“你年轻怎么懂这事?”“我外公是私塾先生,从他的书上学来的。”外公去世前,他勘定了自己的风水之地;家父去世,其安息之地是我勘定的。我自己就是风水先生。
此后,好些办白喜事的人家,都来找我:一人吃饱全家不饿,不要打发任何礼物,管两餐饭就够……

忆到此处,又忆起一件至死不忘的事情。酱园巷有个赌棍,又喜欢嫖的,有次深夜回家,在大郎庙巷口见一低头匍匐的女子,不时晃晃头,用手拨弄一头长发,看背影极美。赌棍心痒痒的,上前调情。
长发女子说:你走开哟,别让我吓了你哟!

娇滴滴的回音,让赌棍越发动心,遂上前去欲拨弄头发、抚摸脸颊。还未摸着,长发女子将头摆正,一脸的滔天凶恶,莫可名状的狰狞,加一个突出老长的舌头,立马将赌棍吓得昏死过去。

天刚拂晓,邻里发现赌棍,叫了好久方叫醒他,开口一说便是:好长,好长呀。从此,落个说话打哆嗦的毛病……每每从那巷口经过,即使胆大包天之辈,也要使劲跺跺脚:
漆黑曲巷夜归人,见个长发遮全身。
心想免费好调情,换得舌僵久呻吟。
说句不怕丑的话,这人是我的亲堂爷爷,与我爷爷是亲堂兄弟。我们家族无人不知无人不晓。
多少年前如此,多少年后何尝不一样!

我妹在南门河淹死前的头一天,我在生产队坐立不安,向队长告假回家。第二天清晨,我清清楚楚看见:我妹站在家里楼梯边的城墙下,像一朵无言的小花,静静的开着,再一看,没了!随即有人急匆匆奔来告我:你妹掉河里了……那是我妹的生魂昙花一现,我是专程回来为她送终的,她临死现一下身,是来向我告别呢,还是在向我表达她沉痛的谢意……
此后,读到申宝峰先生的鬼诗,便觉得多了无限亲切与温馨:
人鬼情未了 ·申宝峰
白衣飘飘入云霄,晚霞滚滚当空照。
两眼含情心不死,痴心人鬼情难了。

人鬼殊途· 申宝峰
白衣长发瘦脸颊,媚眼红唇美如画。
敢问美人何处去,美人答曰黄泉下。
苦酒淡淡入肠烧,闷烟缕缕伴夜聊。
痴心已逝化为鬼,本鬼难道情未了!
鬼舍求贤访蓝郡,鬼话连篇讯无伦。
神出鬼没虚前席,神差鬼错望缘份。

后来呢,逢一酷暑夏夜,陋室酷热无比,连日劳累,欲睡无法入眠,我爬窗而出,窗外一片坟地,遂身靠一坟,坟上青草野花送香,须臾,沉沉睡去。良久,鼾声惊动乡邻,摇醒我说:吓死人了,以为死了人没埋,原来是你这背时鬼……
背时鬼有兴致,其时正是夜半,月悬中天,星光几点,夜静悄悄,月色也好,送凉的夜风多情,送来两首熟稔的诗,在耳畔响起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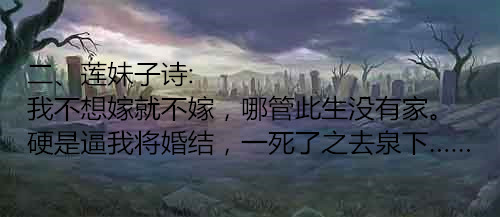
【作者后记】这个人世间,到底有鬼没鬼,恐怕只能等到自己心停眼闭,手脚僵硬,才能揭开这个疑团了!